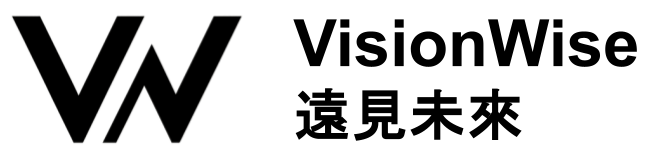民粹主義(Populism)常被描述為一種「人民對抗菁英」的政治訴求。表面看來,民粹強調代言普羅大眾的意見,質疑權威與體制,似乎體現了民主的核心價值。但實際上,民粹政治往往訴諸簡化二元對立的敘事,把社會問題歸咎於特定群體,如政府官僚、移民、富人、媒體等,並以情緒動員代替理性辯論。
社會學家 Jan-Werner Müller 曾指出,真正危險的民粹主義不在於批評制度,而在於它聲稱「只有我們才代表真正的人民」,並將異議視為背叛人民意志。這種「排他性的道德代表性」,使民粹成為一種削弱多元民主的風險力量。
民粹不是一種明確的政治意識形態,而是一種政治手法。它既可以左傾(如拉丁美洲的平民領袖),也可以右轉(如歐洲反移民政黨)。重點在於它如何操作「人民」的概念——用來鞏固權力,還是擴大參與,便見真章。
民粹的心理動力:焦慮、不信任與歸因偏誤
理解民粹的流行,我們不能忽略心理層面的驅力。在經濟轉型、科技變革與全球化浪潮中,許多人的生活確實出現了失控感與不安全感。收入不穩、就業前景模糊、社會階層流動受阻,使得人們容易尋找「替罪羊」,而民粹正是提供了一個簡單的解釋框架。
行為經濟學中有一個現象叫「歸因偏誤」(Attribution Bias),人們傾向於將不幸的結果歸咎於外在可見的他者,例如「移民搶走我們的工作」、「媒體被財團操控」、「傳統文化被現代價值摧毀」。而民粹領袖便透過這種心理弱點,創造出易於理解的敵我敘事,讓人感覺世界變得可控,雖然這種控制只是幻覺。
此外,心理學家 Karen Stenner 提出「權威人格傾向理論」指出,當人們感到社會秩序被威脅時,更傾向支持強勢領袖與簡單答案,這正是民粹主義最容易發芽的土壤。
社會媒體與演算法:民粹情緒的放大器
在數位媒體與社交平台主導下的資訊環境,民粹話語更容易迅速傳播。演算法設計偏好情緒強烈、意見極端的內容,因為這類內容能提高點擊率與停留時間。於是,民粹式的標語,「我們先顧自己人」、「政府都是騙人」、「傳統被摧毀了」便在社群平台上不斷被放大與迴響。
資訊泡泡與過濾氣泡(Filter Bubble)使人們只接觸到與自己觀點一致的資訊,逐漸削弱跨立場對話的空間。而當討論被簡化為二元對立,批判性思維與多元價值就被邊緣化,社會也因而變得更容易撕裂。
以 2024 年歐洲多國的極右政黨選舉表現為例,不難看出社群動員如何在短時間內影響政治版圖。這不是傳統政黨體制的進化,而是情緒操作的新樣態。
民粹的民主矛盾:在制度內破壞制度
民粹的最大弔詭,在於它往往以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實。許多民粹領袖一開始透過選舉取得權力,但當權之後卻削弱制度制衡,挑戰司法獨立、打壓媒體、改變憲政架構,使民主制度內部失去自我修復的能力。
哈佛學者 Levitsky 和 Ziblatt 在《民主如何死亡》中指出,現代民主的崩壞往往不是政變或武力奪權,而是由民選領袖逐步侵蝕制度而來。民粹政治人物以「人民授權」之名否定一切批評,讓反對聲音被貼上「反人民」的標籤,最終讓權力失控。
這點在匈牙利、土耳其、甚至美國等國的民主衰退中均可見一斑。制度看似依然存在,但其精神已被掏空,形同虛設。
我們可以怎麼做?個人層面的辨識與防禦
對抗民粹的第一步,是認清它的面貌。這不只是政治議題,而是一種集體心理的反映。因此,我們必須從日常的資訊消費與思考習慣做起。
- 建立資訊素養:多元閱讀、交叉查證,避免陷入單一立場的資訊泡泡。
- 提升批判性思維:辨認敘事背後的簡化邏輯與情緒操縱,尤其要對「非黑即白」的論述保持警覺。
- 練習不確定性容忍:社會現實複雜多變,接受暫時沒有簡單答案,是成熟公民的重要素養。
- 關注制度設計與政策細節:避免只聽口號,回到具體政策與制度層面評估政見與施政。
唯有當公民整體提高政治心理免疫力,民粹才不會輕易找上門。這雖然辛苦,但比起讓制度一點一滴被蠶食,長遠而言更值得投資。
民主不是意見的總和,而是共同體的修煉
民粹的出現,不只是「人民被忽視」的現象,更是「人民不願再理解他人」的警訊。當我們失去了對他者的信任與對制度的耐心,民主的內核就逐漸凋萎。社會不是只有贏或輸、我或敵,而是需要不斷磨合、協商與修正的共生體。
身處資訊爆炸與焦慮流行的時代,民粹或許難以根除,但我們可以學習不被操縱。我們可以選擇以理性與理解對抗偏見與恐懼。這並非一件浪漫的事,而是一種冷靜、必要、具體的努力。
在下一篇文章,會以更貼近生活、也更實用的方式,從我們日常的角度出發,深入探討民粹如何潛移默化地影響我們的思考與判斷,並提醒自己要如何警覺、不掉進民粹的陷阱。